西方的鸵鸟心态对付不了IS
我们现在正眼睁睁地面对着一场可能会终结人类活动的环境灾难,正如6500万年前那次行星以前所未见的速度撞击地球、摧毁了一切物种的灾难那样——而现在我们就是那颗行星。

【编者按】最新一期的美国左派思想杂志《雅各宾》网络版在11月23日发表了对美国左派知识分子、MIT语言学教授乔姆斯基的专访,涉及的话题非常广泛,从巴黎恐怖袭击、IS到希腊债务危机,从巴尔干问题到社会主义理念。澎湃新闻编译了此次专访中部分内容。
(一)
提问:你怎么看最近的巴黎袭击?怎么看待目前西方打击IS的策略?
乔姆斯基:当前的策略显然是无效的。IS对巴黎袭击和俄罗斯客机坠毁的声明非常明确:你轰炸我们,你就得受罪。他们是一群怪物,这些都是可怕的罪行,但是西方这种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心态并没有什么用。
最好的结果是IS被地方部队摧毁,这有可能发生,但是需要土耳其同意;糟糕的结果是土耳其支持圣战分子,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将是胜利者;最优的结果是缓慢地谈判协商。
不管怎样,IS似乎已经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逊尼派地区建立了相当稳固的地位。他们似乎已经参与到国家建设中,过程相当残酷,结果相当成功。他们赢得了逊尼派的支持,尽管逊尼派可能看不起IS,却把它当成防御更糟糕外部入侵的唯一方式。这一地区主要的反对力量是伊朗,但是支持伊朗的什叶派民兵和IS一样残暴,他们也极有可能支持IS。
事实上,伊拉克战争导致了教派冲突,将这一地区撕成碎片。这也是中东专家、前中情局分析师格雷厄姆·富勒(Graham Fuller)所说的“美国是IS的主要创立者之一”。
可以想象到的任何摧毁IS的方式都基于更糟糕的基础,即与军事干预有关。一战之后英法帝国在该地区施加了西方国家体系,却很少关心在他们控制下的民众,如今这一体系彻底崩溃。
未来看起来很黯淡,尽管在库尔德地区有些许光亮。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减少该地区的紧张局势,限制并减少该地区获得超乎寻常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目前尚不清楚还有多少外部力量介入,除了西方一贯为之的煽风点火。
提问:今年,我们也看到希腊政府通过博弈与债权人达成了协议。有人认为,这损害了欧洲共同体的利益,因为欧盟尝试在工会、希腊社会以及紧缩政策受益者间的争斗下解决债务危机,你同意吗?你怎么看待这种情况?
乔姆斯基:现在还没有强有力的措施来解决债务危机。凌驾于希腊的三驾马车(IMF、欧盟委员会和欧洲央行)大幅恶化了局面、破坏了经济,并且阻滞了可能的经济增长。现在希腊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债务占比已经远高于这些政策制定之前,给希腊人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尽管德国和法国的银行承担着危机中的很大一部分比例。
给希腊人的所谓的“救助”,大多数进了债权人的口袋,这个比例大概高达90%。德国央行前首席卡尔·奥托波尔(Karl Otto Pöhl )认为:“债务注销是为了保护德国银行,尤其是法国银行。”
美国知名杂志《外交事务》的评论家马克·布莱斯(Mark Blyth)直接写道:“我们从来没有理解过希腊危机,因为我们拒绝看到这场危机其实是对金融业救助的延续,从2008年开始,到今天仍然在继续。”
人们已经认识到,现在各方面都无法支付债务。在这场危机刚萌芽时,就应该进行调整,它本该很容易被解决。
德国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这张当代欧洲丑陋的面孔——现在是德国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根据路透社新闻报道,他表示“向希腊注销部分欧洲贷款,也许可以使希腊的债务降到可控水平”,同时他又说“排除这样的情况”。总之,我们竭尽所能榨干你。大部分人都在渴望体面生存的希望下,迷了路。
其实希腊还没有被榨干,银行业可耻的做法和政府的官僚作风使得希腊的资产被贪婪之手接收了。
德国扮演的角色是可耻的,不只是因为纳粹德国蹂躏希腊,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时代周报》上发言:“德国真是一个好国家的最好例子,整个国家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偿还过外债的记录,无论是一战后还是二战后,都没有。”
1953年的伦敦协议,消除了德国一般的债务,为其经济复苏打下基础。皮凯蒂认为这还远远不够“慷慨”,如今德国靠向希腊发放较高利率的贷款再次获益,这是个肮脏的生意。
从经济角度来看,对希腊(和欧洲)的财政紧缩政策是相当荒谬的,而对希腊来说是一个大灾难。然而作为阶级战争的武器,这是削弱福利制度、养肥北方银行业和投机阶层,让民主边缘化相当有效的手段。
如今,三巨头的所作所为是一种耻辱。几乎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坚决地建立起一些人们必须服从的原则:蔑视北方银行业和布鲁塞尔官僚机构的行为将不会被容忍,欧洲的民主思想和大众意志必须被废弃。
(二)
提问:你认为未来发生在希腊的斗争代表了目前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吗——例如,社会需要和资本主义需求之间的斗争?
乔姆斯基:在希腊,以及更普遍的在不同程度上的欧洲,在破坏性的新自由主义袭击下,战后的一些最令人钦佩的成就正在被颠覆。
但它确实可以被颠覆。拉丁美洲的国家是正统新自由主义里最听话的学生,但他们也遭受了最严重的伤害,这一点并不令人意外。
不过,近年来,他们也拒绝正统新自由主义,而且更普遍的是,它们五百年来首次统一采取重大步骤。把自己从(过去一个世纪的美国的)帝国统治之下解放出来,去面对形形色色的令人震惊的内部问题,而这个社会传统上由富有的精英(主要是白人)所管理。
希腊激进派可能标志着类似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它必须那么野蛮。在欧洲和别的地方还有其他的反应,可以扭转局势,通向更好的未来。
提问:再看叙利亚,我们看到一个可怕的人道主义形势和看不到尽头的自相残杀冲突正在发生。你支持禁飞区和强制执行人道主义走廊吗?能阐明你对叙利亚的立场吗?
乔姆斯基:如果针对阿萨德的干预将缓和或结束这个可怕的现状,那它将是合理的。但这可能吗?干预不是经过对现场的仔细观察和对叙利亚现状的充分了解提出的——帕特里克·科伯恩,查尔斯·格拉斯,还有许多其他对阿萨德的尖刻批评者——他们警告说这有可能加剧危机,我认为这种警告有很大的合理性。
一个几乎不能被忽视的事实是,在该地区,军事干预的记录是可怕的,而且是十分罕见的例外。禁飞区,人道主义走廊,对库尔德人的支持,以及其他一些措施,可能会是有帮助的。但当要求军事干预变得十分容易时,考虑到产生的后果,提供合理和深思熟虑的计划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而我还从未见过这样的计划。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干预由良性力量实施,致力于受苦人民的利益。但如果我们关心受难者,我们就不能为这种想象中的世界提出建议,只能为现实世界出谋划策。而在现实世界里,干预往往伴随着罕见的一致性,由致力于自身利益的权力实施,在这里,尽管职业崇高,受难者和他们的命运仍然充满着偶然性。
历史记录是痛苦而清晰的,没有奇迹般的转换。这并不意味着干预永远不合理,但这些因素不容忽视——至少,如果我们关心受难者。
(三)
提问:什么事物给予你对未来最殷切的期望?你觉得如今和你交流过的美国年轻人与几十年前的那些相比有什么不同吗?社会态度是否已经变得更好?
乔姆斯基:对未来的希望总是相似的:有一群有胆量的人,即使在严酷的强迫下也拒绝向精英权威和迫害卑躬屈膝,其他人致力于与不公正和暴力行为作斗争,年轻人则真切地希望改变世界。关于功成名就之人的记载总是非常有限,有时还会被撤销或颠倒事实,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的穹顶总会指向正义,我借用马丁·路德·金的卓越言行来证明这点。
提问:你怎么看待社会主义的未来?是否受到南美洲发展的启发?对北美地区的左派而言是否受到了教训?
乔姆斯基:正如政治学学说的其他术语一样,“社会主义”也可以表示许多不同的意思。我认为人们可以从启蒙运动到古典自由主义(以及鲁道夫·洛克所言“在资本主义残留的碎片之后”),再到社会主义的自由论观点——即社会主义汇聚并引导着无政府主义者的倾向中——追溯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足迹。
我的感觉是,这一传统的基本观点从来没有深埋在表层之下,更像是马克思“身上的一颗痣”,总是要在正确的时机即将到来之时产生突破,并通过行动树立起正确的旗帜。
我认为近几年在南美洲发生的事情具有重大的历史性意义。在西班牙征服者之后,社会第一次开始采取我之前所强调的措施。这一步虽然走得不那么稳,但意义重大。
(对北美来说)主要的教训是,如果社会主义可以在严厉野蛮的情况下实现,那么感谢之前来到这片土地的人们,我们应该继续做好本分,享受因此而得到的自由和繁荣的遗产。
提问:你同意马克思“资本主义必将最终被自身毁灭”的预言吗?你认为是否有一种可替代的生活方式和经济体系,可以阻止资本主义的瓦解?普通人应该担心哪些问题呢?
乔姆斯基:马克思研究的是一个抽象的体系,其中包含了一些真实存在的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但没有包含其他的,包括国家在发展方面决定性的角色和持续进行资本掠夺的机构。
大规模的国家干预已然是发达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从英国、美国、欧洲到日本及其前殖民地形态直到当下的状态。例如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技术,很多被开发完善的机械中都可能保留着现存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
现存的体制很可能由于很多不同原因而摧毁其自身,这一点马克思也已谈论到了。我们现在正眼睁睁地面对着一场可能会终结人类活动的环境灾难,正如6500万年前那次行星以前所未见的速度撞击地球、摧毁了一切物种的灾难那样——而现在我们就是那颗行星。
普通人(我们每位都是)可以努力去阻挡那并不遥远的灾难,并创建一个更加自由而正义的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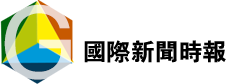 国际新闻
国际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