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恐怖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同属虚无主义
或许只有以“诚”和“仁”为根本的中华文明,或者与之相通的,以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为原则的共产主义,才能拯救和扬弃已然深陷困境的现代资本文明。

就在巴黎恐怖事件发生前的周五傍晚,我参加了复旦大学“政研”中心组织的“网络时代的政治与安全战略”沙龙,我的主要观点是:即使在网络和现代技术日益普及化的今天,危险的本源仍然是现代社会日益的犬儒化和虚无主义,以及由之导致的社会关系的日益分裂和对抗性本质,形成了在神圣宗教的名义下进行的宗教暴恐活动日益频繁,网络和技术不过把这种危险日益扩大了。一语成籖,当天晚上巴黎就再次爆发了恐怖主义暴力事件。恐怖分子在巴黎巴塔克兰音乐厅、法兰西体育场等多处进行了7次枪击、6次爆炸袭击,高喊“为了叙利亚”和圣战口号,目前已造成百余人死亡,世界仿佛突然回到了2001年9月11日。
恐怖主义根源之一: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导致的社会对抗性
如果抛开表面的宗教差异和文明对抗,我们就能发现这背后的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根源。最主要的根源之一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导致的社会对抗性。同样就在恐怖事件发生前一天,法国著名政治哲学家伊夫·夏尔·扎卡教授(Yves Charles Zarka)在《欧盟的理想与危机》的演讲中,就曾分析了西方目前面临的经济危机、新形势的恐怖主义危机以及移民危机之间相互交织的状况。在经济上,由于过于笃信市场看不见的手的自我调节机制,政府看得见的手日益迷失,对教育、环境、公平等关乎民众福祉的公共领域缺乏治理能力,在资本和市场逻辑的疯狂舞蹈之下,欧洲日益陷入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实质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商品又日益积压而无法销售出去,并由此引发了错综复杂的社会、文化危机。就如另一个现代性思想家汉斯-彼得·马丁数年前在《全球化陷阱》中所言:新自由资本主义的许诺往往只是“动听的谎言”,只会导致“无法无天的社会反常状态,使社会结构崩溃,而这些社会结构的正常运转本是福利社会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
西方社会日益陷入货币和资本拜物教之中无力自拔:人们沉迷于权力与利益的争斗之中,成为货币符号的奴隶,把他人当作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就如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所说:以现代资本文明为主宰的“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他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一切癖好、一切秉赋、一切有关出生和幸运的偶然性都自由地活跃着”。市民社会的“个体性”非但不是个性,其“本质上是含有否定性的”,是“排他性的自为存在”。他遵循的是自利的自我保存原则,而不是共享原则。马克思同样指出,现代社会的货币关系排挤了人身关系,人的一切活动都被转化为交换价值并遵守交易原则,在货币关系中,在发达的交换制度中,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育差别等等事实上都被打破了,人伦关系因此遭到了解体和没落,传统的伦理和道德在其中瓦解,而代之以自私自利和唯我主义,人们之间变成了普遍的效用关系。如果说马克斯·韦伯只是哀叹现代世界中“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的话,如果他活到今天,就会更加失望地发现,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早已被货币这一现代世界的上帝所侵染,直接的亲密的人与人的关系,早已如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荡然无存。
恐怖主义根源之二: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虚无的神圣
因此,根源之二可以说是现代资本文明无法提供人们对崇高、审美和永恒的根本性渴求。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对任何理想和崇高的元叙事都视为“强制”、任何对普遍人性或孟子的“四心”追求都变得日益不可能,宗教和文化也不再与普遍的人性超越相关,坚守良知的人被嘲笑为傻帽和愚笨,耽于虚无缥缈的人性而不懂得自己的真正利益之所在。不管内心的焦虑还是对良知的笃信,都被当作是过时和守旧的象征,那些值得敬佩的有关意义与生命的问题,都被作为虚幻而有害的天真被丢弃。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和宗教现象的消失,相反,其文化现象纷繁复杂,比如同样还有各种宗教、文化组织,只是其核心原则已经转换,所呈现的是一种贫乏的“繁荣”、虚无的神圣:人们随意从一种宗教改信另一种宗教,或者干脆直接把宗教和文化视为文化和娱乐消费的对象,理想主义的力量日益衰落为精致的利己主义和犬儒的消费主义,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无法体验真理和实现精神与灵魂的安顿,原本诗意而崇高的“心安理得”变成了麻木的“心安理得”。
在一片消费主义的狂欢中,文化、审美和宗教完美地与商业结合起来,日常生活由于广告和产品设计而“审美化”了,只是这样的文化,不再与崇高有关,有如伊格尔顿在《文化与上帝之死》中所言,对后现代的资本主义而言,“唯一剩下的就是商品和名声了”。宗教似乎早已衰落成了无关紧要的私人娱乐消遣活动。有如收藏古董或养育小动物,再也难以与崇高的生命体验相关。上帝的王国让位于拍卖行,当代社会正向无神论和世俗化的方向奔涌前行。这种虚无主义是骨子里的,在虚假的宗教和文化繁荣背后,是对文化信念或希望的完全不在乎,对尼采来说,其遵循的是对“高价值的自我贬黜”的“堕落的逻辑”,其是“精神力量的衰退”。社会的团结与正义正日益远离人们的生活。人们只求成功不求伟大,追求鲜亮的平庸和坚持精致的利己主义,不再相信真理、良知,犬儒主义、虚无主义、市侩主义成了时代的精神境况。 因此,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10年不无无奈地宣布:文化多元主义在当代欧洲已然“彻底失败”。
其实,早在《资本论》1857年第一版的序言中,马克思就已指出这种后现代文化的虚无主义本质,即其核心特征仍然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比如英国高教会宁愿饶恕对它的三十九个信条中的三十八个信条展开的攻击,而不饶恕对它的现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进行的攻击。在今天,同批评传统的财产关系相比,无神论本身是一种很轻的罪。有如海德格尔所言,人们只追求“存在物”而遗忘“存在”,或者不再带有深深的感激之情铭记“存在”。这样一来,“伦理的东西已然丧失”,彻底的私有财产化给人们的交往强加了一个抽象的框架,并且错误地一味追求抽象的货币,而不顾家庭和社会伦理共同精神。这种抽象的框架却令人们彼此疏远和冷漠,甚至最亲密的人际关系都退化为金钱得失的计较,人们也被分割为互相争斗的利益斗争者。最终的结果不是对人的普遍肯定,而是普遍否定。这种普遍否定的失败和无意义之感,形成了人们对现代虚无主义的强制性反抗,试图通过追求极端而纯洁的宗教信仰来完成对虚无主义的克服,只是这种路向从一开始便已然错误。
恐怖主义根源之三:共同的“异化”
现代宗教暴恐案件的频繁,根源之三在于对信仰和生命救赎之路的极大误解。“伊斯兰国”的宗教恐怖主义虽然谴责西方的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但其本质上却同样陷于另一种变形的“异化”之中不能自拔,表面上甘于奉献和牺牲的英勇姿态在把他人当作手段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用他人的生命来为自身的所谓信仰来狂欢作乐。初看之下,作为感官欲望的宗教的现代资本文明和与其相对的原教旨主义在走向两个极端,前者满足于物质生活和货币符号,另一方则满足于某种超验理念。但实质上两者共同的特点都是停留于抽象性的“客观幻象”之中,货币或极端宗教“抽象”成了人们现实生活的一个超个体的现象和先验性存在,最终的结果是不是对人的普遍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将人与人的丰富的关系,崇高和审美的情感全部消解掉了。一切个性,一切特性都已被否定和消灭的一种一般的东西。齐泽克曾经在《洛杉矶书评》2015年2月23日的访谈中指出,根据伊斯兰国的公开声明,当局明确表示他们的主要任务不在于民众福祉(人口健康、免于饥饿等)——而是“宗教生活”,最重要的是确保所有公共生活遵循宗教准则。这就是为什么看似神圣的伊斯兰国,其本质和资本主义一样,为了抽象的外在化形式,而对人道主义灾难感到冷漠——他们的座右铭是“宗教好,一切皆好”,而非“人好,一切皆好”,人被异化成了宗教的手段,生命本身的崇高和意义从未真正进入他们的视野。
如果说后现代消费主义不被当真的宗教和文化是某种虚无的神圣,或者说把一切神圣和真理虚无化,其在消费主义的货币的异化中,仍然永远遗忘生命性的存在和人本身的话,宗教恐怖主义则是神圣化的虚无,原教旨主义者在其神圣化的宗教话语和信仰中,仍然将人本身视为手段,而不是目的。他们只能在物质享乐主义者愚蠢的镜子中看到自己。威廉•巴特勒•叶芝的诗《基督重临》恰如其分地描写了当代困境:“优秀的人们信心尽失,坏蛋们则充满了炽烈的狂热。”“优秀的人”一味追求成功而忘记伟大,从而失去了生命和生活本身,而“坏蛋们”则煽动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的宗教狂热,最终同样失去了对生命和生活本身的热爱。“伊斯兰国”对其理想信念极端执着的原教旨主义做法,恰恰失去了人之为人的真正的信仰和灵魂,更谈不上爱和真诚,他们滥杀无辜的暴力行为证明了自身是一种漠视生命的“绝对野蛮”。原本提倡牺牲和奉献精神的宗教文化,就被恐怖组织曲解为自杀式袭击和对生命的无情杀戮,宗教和神圣从而被用来为野蛮暴行正名。
现代资本文明与恐怖主义:虚无对抗虚无
对宗教暴恐事件频发进行分析的基本结论是:这种由现代资本文明的虚无主义所引发的对抗与冲突,并非是“两种文明之间由于理想、价值观、宗教或其它因素引起的对抗。” 也不是两个不同历史时代之间的冲突,即伊斯兰国的宗教恐怖主义并非前现代力图对现代化进程进行极端抵抗的原始野蛮行为,两者冲突并非“属于中世纪的心理和21世纪的思维之间的冲突”,或者所谓先进和落后、文明与原始的冲突、理性与野蛮、自由与压迫、民主与专制的二元对抗。伊斯兰国的宗教恐怖主义应当被视为诸如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倒错的现代化现象,他们同样热衷于现代的物质、技术文明、量化规则和科层化制。其和现代资本文明表面上的二元对抗,本质上是用一种虚无主义的方式来回应另一种虚无主义,实质上都同属于虚无主义的范畴。是“同一种文明”内在化的对抗,据法国参议院早前出具的一封报告,已有超过三千多名欧洲圣战分子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为IS效力便是明证,表面上的不同宗教和文明冲突遮盖了资本主义日益面临自身难以克服的危机和挑战的窘境。它导致在欧洲出生成长的一些年轻人对于自己的国家产生了非常强烈的憎恶。而某种宗教的神圣性正是可以为自身的虚无主义仇恨找到崇高性外衣的绝佳路径。因此,极端世俗主义与极端宗教主义这两个看似对立的主张,其共同的本质是对人性和生命情感的虚无主义态度。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本质上是“内在信仰虚无主义”,而极端宗教恐怖主义则是“外在信仰的虚无主义”。
在笔者看来,或许只有以“诚”和“仁”为根本的中华文明,或者与之相通的,以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为原则的共产主义,才能拯救和扬弃已然深陷困境的现代资本文明:迷恋极端的原教旨主义的超越性是可笑和可悲的,相信必须停留在现代资本的那种完全的空虚化之中,也是可笑的。正确的做法是扬弃两者的非此即彼和简单,重建人之为人的文明新类型。其将不再仅仅是政治意识形态的真理,更是全球政治的“一般方向”和人类的真理,它是自古以来对善的追求与坚守,首先意味着对人类平等和团结原则的强调,其次,它意味着对集体性原则的肯定。它也意味着人的真正依归和灵魂的安宁,既非现代人的虚无、孤独和寂寞,又非极端宗教的狂热主义,而是一种心有灵犀的相通性,从而克服人与他人的分离,超越了政治与经济、宗教或艺术、日常经验之间的分裂,它并不会吞噬所有的具体性,消解一切确定的形式,而是真正的和而不同。如果著名的现代性问题研究专家艾森塔特所述如实的话,即野蛮主义潜藏于现代性的内核之处,或者说是现代性的内在本质:通过实存力量而非道义来获得承认。新文明类型则始终把坚守道义与和平共享放在首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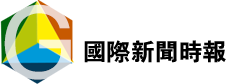 国际新闻
国际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