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理解的国学
以“生”为根柢、以“道”为纲维、以“觉”或“觉悟”为要径的国学,其研究或教学自当是生命化的。所谓“生命化”,简而言之,即是把知识的授受、智慧的开启导之于生命的点化或润泽。

——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建院十周年庆典的演讲
“生”:国学之根柢
追溯载籍或文物可考的古昔,中国人可谓自来即重“生”。这对生命的看重和对生命之秘密的寻问,是别有宗趣的中国人文意识得以发生和持存的契机所在。
迄今我们可以得到的古人重“生”的最早消息,是由殷商时期即已存在的“帝”崇拜活动所报导的。“帝”字的写法在甲骨文中大体定型,经心于卜辞考辨的学者们或以其所指为当时殷人的至上之神,或以其所指为尚未达到至上地位的诸神之一。但没有多大问题的是,即使只是把“帝”视为诸神之一,它也是诸神中愈来愈引人瞩目而对当时和后世中国人心理影响最大的一位。况且,肇始于殷商甚至更早一个时期的“帝”崇拜原是一个持续着的过程,这个由周人承其绪的过程毕竟愈到后来愈益显现出“帝”在人们心中那种非他神所可替代的至尊地位。事实上,甲骨文中的“帝”也是花蒂之“蒂”,“帝”由神化花蒂而来,而花蒂为先民所神往则在于它是植物结果、生籽以繁衍后代的生机所在。宋代史学家郑樵谈及“帝”字的构形时曾指出:“帝,象华(花)蒂之形。”(郑樵:《通志略·六书略》)此后,清人吴大澂解“帝”字说:帝,“象花蒂之形……蒂落而成果,即草木之所由生,枝叶之所由发,生物之始,与天合德,故帝足以配天。”(吴大澂:《字说·帝字说》)。如此由花蒂之“蒂”解“帝”,几可说是对渊源有自的“帝”崇拜这一千古之谜的道破。有趣的是,在“帝”崇拜发生的时代,“生”字业已出现。甲骨文中的“生”字,上半部分象草木生发之形,下半部分则是摹地表之状的一横;它表明古中国人的“生”的初始意识是萌发于草木的生殖的,而这则正可与“帝”崇拜由之衍生的花蒂的神化相互说明。
如果说“帝”崇拜是对古中国人生命崇拜意识的一种隐喻,那么产生于殷周之际的《周易》则可视为这传承中的生命意识的一种象征。“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系辞上》),这“生”的过程是依次把“太极”、“两仪”、“四象”按“阴”、“阳”两种动势尽分于“二”的过程,而六十四卦是依“阴”、“阳”两种动势第六次尽分于“二”的结果,它象征着万事万物的“多”。比起古希腊人由万物“始基”的悬设所引出的“一是一切、一切是一”的哲学智慧来,中国的“帝”崇拜与《周易》古经对“一”和“多”关系的默示是另一种情形:在神化花蒂的“帝”崇拜之潜意识中,花蒂是“一”,由花蒂结果所生的种子是“多”;在《周易》古经中,“太极”是“一”,由“太极”依“阴”、“阳”两种动势所生之八卦、六十四卦是“多”。古希腊人由万物“始基”所推演的是一种宇宙构成理论,古中国人从“帝”崇拜到“生生之谓易”(《易·系辞上》)所成就的是一种有机生成观念。“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系辞下》),《易传》的这个说法道出了中国人文意识中最深切的理致,也道出了中国人文意识中最动人的情致。
从一定意义上说,有了文(文籍)献(贤者)就有了“学”,今人所称之“国学”可以说是发轫于古人重“生”的那点灵韵的,这灵韵为后来愈益显现出其独异精神性状的中华学术文化培壅了“阴”、“阳”化“生”的致思根柢。
“道”:国学之纲维
“生”不能没有必要的环境条件,因而它首先是有待的。生命的有所待因为外部变故的难以预期、难以操控而给人以一种无常感,这使人这一唯一达到了对“生”的自觉的生灵产生了“命”意识。春秋晚期以前的中国人所顾念的“命”主要落在一种或然性或偶然性上。它为人留下了一定分寸的选择的可能,于是以占筮方式作人事决断的古代中国遂有了关系到天人之际的“史巫之学”。
不过,“生”在人这里还有另一个维度,它是相对于有待维度的无待维度。人生有待维度的问题主要是生死、利害问题,人生无待维度的问题主要是人格、品操问题;人在人格、品操上的提升对外部条件无须依赖,因而人生的这一维度无所待。与人生有待维度上的“命”意识相对应,伴随着人生无待维度的自觉,中国人开始关注人成其为人的所谓“性”。与人的“命”意识相始终的是人对死生、富贵价值的欲求,由人的“性”意识的自觉所引出的是人对自己心灵境界的看重。于是,因着对人生两个维度及这两个维度上的人生价值如何对待、如何引导的问题的提出,春秋战国之际产生了所谓“道”这一意趣隽远的运思范畴。
“道”字不见于甲骨文,金文中“道”的最初寓意是寻路或辨路而行。寻或辨涉及行路方向的选择,所以“道”的本意当如唐人陆德明所说:“‘道’本或作‘导’。”(陆德明:《经典释文·尔雅音义》)清末民初以来,学者们多以宇宙本体诠释“道”,也有人以所谓规律性理解“道”,从“道”的字源到“道”在老子、孔子那里的运用看,我以为,还是把它从功能——而不是实体——意义上领悟为虚灵的“导”更妥当些。
“道”在“导”的意味上有朝向性,有实践性,所以它主要是一个与人的生命体验息息相关的实践范畴,而不可将其执著为一个思辨性的认知范畴。此外,我要指出的是,“道”在老子、孔子这里都已有了“形而上”的品格,《周易·系辞上》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即是就此而言。
与老子、孔子前后古代中国人心灵眷注的焦点“由‘命’而‘道’”的移易相应,中国学术的主流由先前的“史巫之学”渐次转为“为道”或“致道”之学。孔子对于《易》有“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马王堆帛书·要》)之说,其实,曾为“周守藏室之史”而终于“自隐”做了“隐君子”的老子,与囿于数术的史巫们又何尝不是“同途而殊归”。老子“尊道而贵德”(《老子》五十一章),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皆以“道”而“道德”为其学说之要归。自此以降,先秦以至晚清的诸子百家之学几乎无不在孔、老——两汉之际佛学西来中国遂有“释”——之学所构成的运思张力的笼罩下;先秦儒家倡言“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其实“学”而“致道”的旨趣在抽象的意义上又何尝不为其他诸家之学所恪守。
“觉”:国学之门径
随着“道”作为一个虚灵而至高的致思范畴在孔、老时代的出现,“学”之为“学”本身亦愈益臻于自觉。“学”的本字“斅”在甲骨文中已见雏形,但其或可能指示某种祭祀活动,或用于人名,学之为学的涵义似尚在朦胧处酝酿中。“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书·周书·多士》),这“册”、“典”当指甲骨卜辞、刻辞的有序辑集,而卜辞、刻辞及其有序辑集即隐示着学问或学术意味上的学的萌朕。诚然,最早的勉可以学术视之的学只是史巫之学,但当着“与史巫同途而殊归”的老子、孔子扬弃数术而立“教”以称“道”,一种属意于人生意义而竟至把与人生相关的一切皆辐辏于此的学问产生了。差不多同时,“学”在被反省中有所自觉,问学的契机与途径亦开始被留意。
《说文》释“学”:“学,篆文‘斅’省”,“斅,觉悟也”(《说文解字》卷三下)。《广雅》释“学”:“学,觉也。”(《广雅·释诂四》)不过,此所谓“觉”或“觉悟”绝不是离群索居者的苦思冥想所能奏效的,所以《广雅》又释“学”:“学,效也。”(《广雅·释诂三》)“效”不是为效而效的那种外在模仿,而是为了“觉”,因而“效”的过程也是“觉”的过程。朱熹注《论语》“学而时习之”之“学”时就说过:“学之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朱熹:《四书集注·论语集注》卷一)诚然,明确以“觉”或“觉悟”释“学”是汉以降的儒者之所为,但“学”之“觉”义则早已见之于春秋战国之际的典籍。
“觉”意味着所“学”对于“学”者的心灵有所默示而对其生命有所触动,这“学”而“觉”之的祈求决定了自觉于春秋战国之际的中国人的学问的精神性状。它的重心不落于知识的记诵,也不落于概念的推理,而是在于生命的感通。“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孔子这句托重古人以强调“学”而“为己”的话是就儒学旨归于人的心灵境界的提升而言的,老子不曾有过类似的说法,但道家之学的趣致依然在于人的灵府的安顿。儒家“依于仁”,道家“法自然”,孔、老虽价值取向异趣,但都因其发于生命的价值祈求而使其学说同为“觉”或“觉悟”之学。“道”在春秋战国之际作为系着人生终极趣向的虚灵而至高运思范畴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历史文化的“轴心时代”(雅斯贝斯语)的莅临,它从大端处决定了往后的中国学术或学问——近现代人称其为“国学”——的非以逻辑思辨为能事的“觉悟”的品格。
以“生”为根柢、以“道”为纲维、以“觉”或“觉悟”为要径的国学,其研究或教学自当是生命化的。所谓“生命化”,简而言之,即是把知识的授受、智慧的开启导之于生命的点化或润泽。我曾说过:“‘道’只在致‘道’者真切的生命祈向上呈现为一种虚灵的真实。只有诗意的眼光才能发见诗意,历史中的良知也只有当下的良知才能觉解……不论是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物,都只能活在富于生命感的阐释中,阐释者从阐释对象那里所能唤起的是阐释者自身生命里有其根芽的东西。虚灵的人文传承也许在于生命和历史的相互成全——(此即)以尽可能蕴蓄丰赡的生命由阐释历史而成全历史,(也)以阐释中被激活因而被升华的历史成全那渴望更多人文润泽的生命。”(黄克剑:《由“命”而“道”》初版自序)我在今天这个场合重温这些话,固然主要在于自我警策,却也期待以之与眼下从事国学研究与国学教学的诸位同仁、同道同途共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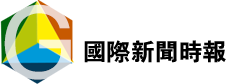 国际新闻
国际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