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性”商业竞争与无力自救的患者
原标题:“恶性”商业竞争与无力自救的患者
2019年的冬天,在洛阳栾川县冷水镇东增河小学门口,13岁的程智斌双手扒拉着大门的铁栅栏,他的大眼睛透过栅栏空隙,忧郁地望向几栋教学楼。
五年前,程智斌小学一年级时,母亲杨艳丽每天带着他从大山沟的家,走半个小时,到村上的小学上学。但很快,他们就不用再花半小时去学校了。那年除夕,程智斌被查出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此后,全家过上了四处筹钱,四处求医的日子。
2019年11月25日,为了凑钱做手术,父亲程海波为儿子发起了第三次网络筹款。
五天后,一则《卧底实拍医院扫楼式筹款,审核漏洞多》的视频在网上传播,视频中揭露了一款大病筹款平台“水滴筹”线下推广人员募捐金额填写随意、审核不严、求助故事有模板,和被要求“末位淘汰制”等问题。
舆论在网络上不断发酵,大病筹款平台引爆公众信任危机,水滴筹宣布全面暂停线下服务,同类平台亦然。
从2014年兴起,大病筹款平台已高速发展了五年。但在这五年里,商业与公益,一直是这个行业难以掌控的一块平衡木。往上不断加码的还有:行业监管的“无法可依”、恶性的商业竞争以及无力自救的患者们。
在危机来临后,影响最直接体现在那些筹不到钱的患者家庭身上。他们永远是沉默的一方。
医生不断催着程海波和杨艳丽筹钱给孩子做手术,拿出30万手术费,就能立马把孩子推进手术室。
但12月17日,大半个月过去了,他们只筹到442元。
一个网络募捐的时代
2014年1月30日下午,程海波带儿子赶到河南省肿瘤医院时,他们成了那天最后一个病人。第二天,就是春节。
7岁的程智斌被确诊为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为了赚钱给孩子治病,程海波坐上去甘肃的火车,去做矿山出渣的体力活,他打听到石家庄的医院能治这个病,让妻子杨艳丽带儿子去石家庄。
在甘肃时,程海波给主治医生打了个电话,对方说这是血液科最轻的病,两年内能治好,花费大概是十七八万。“我说那行,就在这儿治。”程海波说,“当时我就下定决心,赚钱把娃子的病治了。”
半年后,程智斌的病情稳定,杨艳丽带儿子回家。此后两年,程智斌以药为生,每月药费需要五千多元。但程海波因打工过度,腰椎间盘突出,无法再从事重活,只能回老家打零工。杨艳丽为了孩子能做脐带血移植,怀孕两次,均失败。
也在程智斌确诊的这年,北京的创业工程师周汉突然被查出急性肝衰竭。他的同事通过众筹平台轻松筹发起“拯救创业攻城狮”的筹款项目,消息在创业圈与技术圈炸开,一个晚上,筹得30万。
2014年,众筹是互联网创业的风口之一,每个月有七八家平台诞生,众筹项目五花八门,传播场景集中在个人微信朋友圈。世界银行发布《发展中国家众筹发展潜力报告》,预计到2025年,我国众筹行业的市场规模将达到460亿-500亿美元。
周汉因术后感染,抢救无效去世,但大病筹款的互联网传播势能被挖掘,轻松筹也将业务方向调整聚焦至大病筹款。爱心筹、无忧筹、诺言筹、细雨筹、水滴筹等大病筹款平台纷纷上线,开启了一个网络募捐的时代。
水滴筹作为首个0手续费的大病筹款平台,发展最快。2017年6月上线后10个月内,四万多人发起筹款,近两千万用户捐助了十数亿元。
2017年11月某日下午3点,程海波第一次接触水滴筹,攥着手机为儿子申请筹款,一直琢磨到凌晨两点。
这年冬天,程智斌不断高烧流鼻血,之后晕厥,送急诊。有一夜,程智斌吐血四次,医生说不行了,但最后还是抢救了回来。杨艳丽回想起这天夜里,哭得泣不成声。
医生说,做ATG(抗胸腺细胞球蛋白)治疗应该能治好程智斌的病,但需要十几万。程海波向亲戚朋友借遍,也就“万把回事儿”,远远不够。嫂子对程海波说,你弄个水滴筹试试。
凌晨两点,程海波终于把所有资料都填对,筹款成功发起了。入睡前,他将水滴筹转发到朋友圈,他看到很多人在这个平台上筹到十几万。程海波心里念着,只求老天爷了。
一个月后,程海波在水滴筹筹到1万6,加上村里学校、大队和镇上企业的募捐,七拼八凑到五万块。程海波带着钱去求村主任,让村主任去医院说情,钱慢慢还,才给孩子上了ATG。
一份“满足对工作一切幻想”的职业
2019年10月,程智斌ATG治疗失败,开始每月输血小板维持生命。杨艳丽要带着儿子坐班车翻过大山,再坐大巴才到得了洛阳市里的医院。医生说,孩子只剩下最后一步,就是移植,需要三十万。
在洛阳的医院,程海波遇见了悟空筹的筹款顾问韩甜甜。
程海波已经不想众筹了,他觉得两年前已经发起过一次了,该捐钱的人都捐了,筹不到钱了。
韩甜甜和同事开车去了程海波山沟里的家,外面下雨,屋里也下雨,喝的水都不干净。她坚持让程海波筹款,还帮助他们申请低保户。第二次筹款,程海波筹到了七千多元。
“最土的不就是这话——帮助他人还能赚钱。”韩甜甜说,2017年,随着网络筹款平台的兴起,线下推广人员的就业市场慢慢被打开。
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在医院里遇见了一个20多岁急性白血病的孩子——妈妈跟别人跑了,爸爸死了,家里只剩一个残疾哥哥照顾他。他写了一篇《如果可以,我想活下去》的文章,韩甜甜的朋友是轻松筹的志愿者,帮孩子发起了筹款。
韩甜甜觉得这工作可以帮人,便加入其中。
但做久了,她发现作为一个新兴行业,筹款顾问们总要面对各种质疑:有些患者觉得天上没掉下来的馅饼,筹款顾问们不是骗子就是传销;有的患者没筹到理想的金额,就会埋怨,说难听的话。
但更难忍受的,是医院无声又压抑的氛围。
最开始两个月,韩甜甜不敢一个人去病房,“都是去比较严重的科室,浑身插满管子,阎王爷挂着号的人。”
韩甜甜见过一个膀胱癌患者,为了不想拖累孩子,偷偷攒安眠药;见过全家患病,大人们放弃治疗,出去打工给孩子治病;见过很多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男人,在放弃对家人的治疗前,躲在安全出口的楼梯里号啕大哭……
做筹款顾问后,林丰(化名)也不断地见证贫穷、疾病、死亡和绝望。
2018年初在北京培训时,他听见CEO沈鹏对台下员工说企业愿景——“帮助亿万家庭”。林丰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份“满足对工作一切幻想”的职业,又能帮助人,又有收入。
“工作前半年,我觉得自己就和救世主一样,比家属还激动。”那一年,林丰家里挂了十多面患者送来的锦旗,墙上红艳艳一片。
他的手机备忘录存着一千多篇为患者写的求助文章,每个字都是他自己打出来的。后来行业危机爆发,“故事模板”被人诟病。林丰说:“用模板说明他们偷懒,把众筹做得很机械化。毕竟幸福的家庭千篇一律,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同。”
林丰记得一个化疗到一半没钱的老人,病友联系林丰,赶到医院时,老人已经坐上回县城的大巴了,电话里说,“算了,不治了”,就挂了。
“我才发现,原来你改变不了什么,你起到的作用,并没有你想象的大。用电影《我不是药神》里的话说,这世界上最大的病,是穷病。”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专题调研组《关于脱贫攻坚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显示,2018年底,中国还有1660万贫困农村人口。这也构成了大病筹款平台的用户画像,多是来自三、四、五线城市的困难家庭。在林丰所在的西部三线城市,他常常看到,孩子病了,父母买个馒头在外面吃完,再回医院给孩子买好吃的。
这两年,韩甜甜在医院看到,一些平台的筹款顾问的脚步变得匆忙。一线员工在医院里扫楼,发传单,送爱心赠品,迅速占领了以三、四、五线城市及以下区域的“下沉市场”。
2018年是大病筹款行业高速发展的一年。民政部指定的20家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募集善款总额超过31.7亿元,同比2017年增长近三成。行业最大的两个平台——轻松筹和水滴筹,上线三年后,均筹款超过200亿元。
小白(化名)在江苏做水滴筹筹款顾问时,平均每月能发起七八十个筹款。他的工作常态是每天跑四五个医院,十层楼来回爬十回,走每个病房、每条楼道,从1床走到55床,每天的步数都在3万步以上,一个月顶多休息一两天。
医院跑多了,就会有医生或护士直接让他去某个病床发起筹款。之后再跑ICU(重症加强护理病房),去血液、肿瘤和神经科这类重点科室扫楼。
做筹款顾问三个月,小白开始流鼻血。在医院要戴口罩,口罩一拿下来,全是血。医生说是劳累过度。鼻血流了三个月,小白选择了辞职。
下沉市场里的商业竞争
三个月前,林丰也选择了辞职。他受不了医院压抑的氛围,也无法接受越来越商业化的行业竞争,“有点像‘百团大战’,恶性竞争。”
林丰听闻了很多抢患者、抢医院地盘的事例。他说,地区负责人说要“建立医院壁垒”,“就是保证市场占有率,不让别的平台发育起来,让我们和患者、医院搞好关系。”良性的尝试是在节日时,和医院科室合作表演节目,或者派送小礼物。
但在极端情况下——有的平台为了追求数量,一个患者重复发起;有的平台员工专门干扰别人工作,“你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你跟患者介绍自己,他也介绍自己,还有在患者面前吵架甚至打架的。”林丰记得。
2018年底,水滴筹实行“末位淘汰制”,要求每人每月最低35单。林丰基本每月能做40单。“但有了要求后,就不是自我驱动,更像在一个销售公司。”
韩甜甜觉得,在一些同行身上总是有一种慌张感。有一次,她发现有同行把其他筹款公司的展牌丢了。还有一次,韩甜甜帮患者用个人的方式发起了水滴筹,等水滴筹的筹款顾问赶来知晓后,一脸生气地问:“为什么不等我帮他发?”
“把我们当销售业务员,我觉得是水滴筹最不需要的东西。”林丰想到自己在医院里对病人介绍是志愿者,但发起筹款更像是在赶业绩,觉得讽刺。
“实际上我们做调研时,我对水滴筹的人说过,我对这种志愿者的‘地推模式’持反对意见。”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马剑银对新京报记者说,“因为存在角色混淆,‘地推’和志愿者,两者的行为基础完全不一样。‘地推’就是按人头赚钱。用商业的KPI模式去推广。”
2019年6月,水滴筹线下服务团队“志愿者”改名为“筹款顾问”,并在12月10日回复新京报记者强调,改变绩效导向考核方式,严厉禁止故意混淆使用“志愿者”名称,应称呼“筹款顾问”。
马剑银指出,虽然水滴筹属于“非营利”板块,但具有“营利”的属性。根据公开资料,水滴公司有三大主要业务板块:水滴筹、水滴互助和水滴保险商城。
“这三层是逐步发展起来,每一层的客户黏性越来越弱,但是每一层越来越赚钱。”中国社科院保险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解释了这一商业模式:“现在的筹款和互助平台几乎不赚钱,但可以向保险业务做客户引流。”
12月5日,水滴筹CEO沈鹏发表公开信称,启动水滴筹业务不久,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网民健康保险意识的教育场景,借助水滴筹能正确普及进行保险保障的价值和必要性。
“理解商业保险,并且去购买,这才是一个常规方案,而不是靠个人救助做最后的解决方案。”清华大学公益慈善学院副院长贾西津认同,她称:“其实这种模式的结合完全没有问题,第一,没有侵犯公益性,即商业保险的推送,没有损害大病筹款的捐助;第二,具有自愿性,不是强制卖。”
但这种商业模式让许多一线人员产生混淆感。林丰碰见不少冲着做公益入行的同事,最终选择离开。
“完不成业绩就天天挨批。”林丰和同事们聊天内容常常是,今天发了多少个,还剩多少个,要怎么弄。当他听说,有人一个月发起有效筹款数达一百多个。他反问:“这是在用心帮助人吗?感觉就是为了工作而工作。”
筹款背后:希望、质疑和犹豫
尽管商业的味道越来越重,但大病筹款依旧给不少人带来希望。
12月4日,在甘肃张掖,王随(化名)半夜咳醒,几次猛烈的咳嗽之后,开始吐血。他立马吞了两粒云南白药和3粒止血药,但忍不住想:止不住血怎么办?会不会咳血的时候喘不过气憋死?
2016年8月,27岁的王随咳血后被查出空洞型肺结核。他来自单亲家庭,17岁就离家打工。医生说,这病得不间断治疗2年,费用在20万。确诊后,王随开始养病,稍稍感觉好些,就出去打工。
今年三月,王随病情复发,查出多耐药,一线药不起作用了,但二线药费用更高。他在兰州送外卖,复发后只能回了老家。
半夜咳血后,王随犹豫,要不要发筹款。他怕身边的人知道他的病,毕竟现在“谈核色变”。他尤其害怕父亲会有意见。“我现在30了也没结婚,而且又得了这病,他可能会觉得在家里抬不起头。”
王随性格自闭,生活中很少有谈心的朋友。写求助文章,是他第一次对外袒露自己的内心。
筹款发起一个星期后,王随筹到四千多元。金额不大,但网络救助平台令他多了些面对生活的勇气。有三分之二的钱来自陌生人,这令他感到一种与外界的连接,“毕竟有那么多人希望我能痊愈。”
距离张掖一千多公里外的绍兴,朱昱看到每个大病筹款都会捐上20元。
但他有点矛盾,认为至少五成的筹款家庭可负担费用,并无需筹款。又想,万一人家真的需要帮助呢?
2017年,朱昱回家照顾急性白血病化疗结束的母亲,父亲躲开家人,偷偷发起了水滴筹,发到朋友圈时,还特别屏蔽了三个儿子。
三兄弟里,两个哥哥日子过得紧,只有朱昱做了点淘宝小生意,手头上有些钱。父亲不想给他们添负担。朱昱发现后,很无奈,又可怜父亲,“我有钱,用不着筹款。”
父亲筹到了一万多,几乎都是亲戚朋友的钱。朱昱觉得,网络平台上的个人求助和他理解的没钱看病筹款不是一回事。“扶贫是需要的,可如果本身你是负担得起医疗费用的,筹款还有正当性吗?”
关于筹款的正当性,在2019年5月引发了舆论争议,德云社弟子吴鹤臣脑溢血,在水滴筹筹得百万,网友举报其隐瞒财产。
事件曝光后,韩甜甜开始遇到不少类似的情况。一个50岁乳腺癌晚期的中年女人,本筹到五千多元,却被人电话举报。“她写文章说是普通老百姓,结果有人说她摆地摊卖过凉皮,是做生意的。”韩甜甜很气愤。女人更生气,把钱都退了回去。
一个男人因父亲生病,负债几十万,但他有一套贷款了30年的房子。韩甜甜问他,要不要发个筹款?对方说,不行吧,我们家还有房子。
一个老兵在重症室里呆了二十多天,韩甜甜让他发个筹款,他说,可是我有退休工资。“他一个月退休工资三千,在重症里面一天就七千多。”
“比尔·盖茨愿意求助,那也是他的权利,但是你可以不捐,这是你的选择。”贾西津对新京报记者指出,大家似乎更关心有钱人不能来筹款,而不是去关注平台公布的信息是不是充分,和筹款对象之间有没有明确的协议。“如果筹款对象提供了虚假信息,或故意隐瞒要求提供的信息,这才是最敏感的地方,这种欺骗是违法的。”她说。
在中国农村,筹款也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关于希望的故事,里面布满了中国式的人情与伦理。
韩甜甜遇到过一对夫妻,老婆躺在病床上昏昏沉沉,老头想发筹款,又很犹豫,他拜托韩甜甜,“你能不能不要说我老婆是子宫癌?我怕她看到影响她病情。”文章改了又改,最后写“腹部有肿块”。
另一个得了乳腺癌的女人刷完所有信用卡,找了各种不正规平台贷款,也不愿意筹款。她说,以前在村里也是风光过的人,不想让别人知道她得这个病。韩甜甜说,像你这样一根头发都没有,谁不知道你得病了?
还有些人因为筹款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病情加重。韩甜甜说:“有些人非常着急筹款,但还有些穷得要死的人,却一点也不接受,他们觉得死得要有尊严,把面子看得比命都重。”
信任危机全面爆发之后
11月25日,韩甜甜找9958(中华少年儿童慈善基金会)为程智斌发起了第三次筹款,目标金额为91万元。
他们没想到,五天后,大病筹款行业遭遇前所未有的社会信任危机。此后,行业进入全面整顿阶段,一线人员暂停工作。
现在,韩甜甜把众筹链接转发到群里,有人回她:“以后你不要往群里发了,我们都不认识。”她身边的人也说,以前他们不知道做众筹是怎么回事,现在知道了,以后只给认识的人捐钱。
在医院,也有患者质问她:“为啥我已经那么困难了,你还要赚我钱?”
韩甜甜回:“你那钱没少你一分,我有工资。”
患者说:“你是凭我赚工资了,是我的钱。”
12月5日,水滴筹CEO沈鹏在公开信中写道:“这几天,看到了有些网友把水滴筹理解成了公益慈善组织,其实水滴筹的核心本质是一个免费的互联网个人大病求助工具。”
停工的日子里,韩甜甜深夜接到了一个女人的求助电话。她老公骑三轮车掉深沟里头了,现在在重症病房躺着,医院让第二天就交手术费。女人求韩甜甜过来写个文章发筹款。
韩甜甜电话里回她,现在不让我们去医院了,而且舆论太厉害了,写了文章也筹不到钱。女人说她没办法了,家里四个孩子,最小的才三岁,真的拿不出钱。韩甜甜拗不过,晚上十点多,骑了40分钟电瓶车,赶去医院。
“这种平台本身就是个新生儿,人们得允许它犯错,允许它改进,但是现在把它打死了。”韩甜甜很无奈。
“缺乏监管而已,如果监管得当,它自然而然就进入一个良性循环了。”马剑银对此保持乐观态度。
但目前,对大病筹款平台的监管,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
马剑银指出,根据《慈善法》第35条后半句,“捐赠人可以直接向受益人捐款”,说明捐赠人的行为属于慈善。但从受助人的角度,向社会求助是一个人的天然权利。“所以这两者之间出现了一个割裂。”
“现在民政部也很头疼,老百姓觉得你应该管,但又没有很强的法律依据去让他们监管。”马剑银说。
吴鹤臣事件后,民政部回应媒体称,个人求助不属于慈善募捐,不在民政部法定监管职责范围内。只有当个人求助平台出现问题引发社会关注时,民政部依据社会热点为由,出面管理。
而大病筹款平台被诟病最多的——对发起人家庭的审核问题,叶永尧律师表示,不论是现行法律还是“自律公约”,均没有对平台的审核和监督责任进行强制性规定。
同时,平台也不具备资格审核发起人的资产等信息。贾西津指出,现在平台能做的是设立和公布自己的规则,与其用户形成“契约”。
信任危机爆发后,对急需钱的病患家庭,个人筹款已经成了一种不抱希望的希望。
12月17日,程智斌的筹款金额就停在了442元,也没涨过。杨艳丽还是固执地在朋友圈转发,每天三四回,但捐钱的人,还没有她转发的次数多。
要是东拼西凑,程海波最多能挤出两千块,这意味着能再送孩子去两次医院,也意味着此后,这个家再也拿不出钱给孩子治病。
杨艳丽只知道网上对水滴筹有质疑,但她没想到,连她的筹款都会受到影响。
为了重建公众信任,水滴筹平台连发四个声明,要改变以绩效为主的考核标准,投入更多力量做好审核。
贾西津说,大病筹款平台是社会阶段性的产物。“我们需要公益的演化,比如医疗制度的完善,保险制度的发达。这些才是制度性的解决途径,而不是每个人病了,靠别人在那儿一个个地去捐。”
而在洛阳山沟中的东增村,程智斌已经很久没去上学了,同龄的孩子已经初中入学,他才断断续续读到三年级。现在,他每天一个人在村里四处转转,性格内向,不怎么和人说话。
接受采访时,他对着手机,怎么也张不开口,杨艳丽在一旁劝他,“他们都是会帮你的好人,你随便讲两句。”
但电话那头,只有沉默。(记者 邵媛媛)
(责编:任志慧、邓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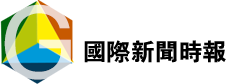 国际新闻
国际新闻 
